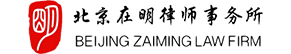- 服务咨询电话: 400-801-9299
- 邮箱:zaiming@zaiminglaw.com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广渠家园5号楼首东国际大厦A座9层901
补偿争议审前和解来了!房屋拆迁补偿争议进入“前调解时代”
- 作者:在明律师
- 来源: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 日期:2020-01-13
导读:只要有房屋拆迁的地方,就会有拆迁补偿争议的分歧,只是分歧者所占比例大小存有不同。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动迁一方通常认为,大部分人都能按拆迁补偿方案签字搬迁,小部分不愿意签字的基本都是想要狮子大开口的钉子户。而被拆迁一方则认为,自家有自家的特殊情况,并非“一把尺子能够量到底”的多数情况,不签是不想越拆越差劲儿。而补偿争议一旦产生,对簿公堂似乎不可避免。近期,补偿争议的审前和解机制开始在一些地方适用,能否通过诉前的调解来实质性化解此类行政争议呢?
实践中,这种分歧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一把尺子量到底”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新中国经历了土地制度改革、房屋制度改革,近年来逐步捂热的城乡规划制度也是刚刚开始从纸面规定着陆,在这种上层制度处于不断进阶的时代背景下,各地土地、房屋登记使用情况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很多征收、拆迁项目在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通常会根据“二八法则”确定一般规定以及特殊情形特殊认定的兜底条款。
实践中,考虑全面程度越高的补偿方案,在推行中的顺畅度越高,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高签约率。反之,那些补偿方案制定没有很好契合当地各种特殊情况以及房价变化情况的,则会陷入三、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也拆不完的境地。
一旦补偿方案是以“长官意志”形态呈现、先天合理性不足,征拆纠纷的产生就被冠上了必然性。近年来,各地政府部门、司法系统开始积极推进建立行政争议调解制度,以疏导调处房屋土地征收补偿、旧城区改造、违法建筑治理、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避免矛盾激化。
《论语·颜渊》有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以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符合我国追寻“无讼”目标的历史民情,也具有降低救济成本、高效便利的客观优势。
然而,前述调解往往是诉中调解,是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阶段,进入司法救济这道最后防线的时候才会触发。这个时候,当事人通常已经在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也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所以调解的诉求已经超出了最初的诉求。
笔者承办的不少案件中,当事人都会坦言,是没有办法才请律师的,如果当初拆迁办能够体恤一下客观情况,自己也愿意降低诉求。只要不吃亏,那个字就可以签。而当律师帮助当事人提起法律程序进行权利救济后,当事人就会默默算账,把“不吃亏”的需求上调到“最合理”的需求这一档。
比起诉中调解,源头治理、诉前调解无疑更为理想。但现实的骨感之处在于,在征收、拆迁项目中,补偿方案的制定很少真正将民主决策、听取被拆迁人意见落到实处。
一旦征收、拆迁程序启动,具体负责实施的征收部门及其委托的拆迁公司往往直接将发出不同声音的被拆迁人视为“钉子户”,并不关心不同声音背后的原因是否合理、如何解决,而是押后处理,等到最后着急用地的时候作为“钉子户”将其上报,再由上级机关通过补偿决定、责令交地等方式强制性收回土地。这种不对等的“信息差”,是大量征拆矛盾的源头。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发现矛盾的第一时间去委托律师帮忙处理。有不少被拆迁人委托律师以后,仍然希望先行谈判、不得已再诉讼。他们认为,律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征收部门、拆迁公司面前摆事实、讲道理、辨析法律,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合理诉求。
然而,现阶段的征收部门及其委托的拆迁公司相关人员十有八九对前述做法予以抵触。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棚户区改造项目曾公然抹黑帮助被征收人表达意愿、进行权利救济的律师是“黑律师”。很多律师同行也或多或少遭遇过陪同当事人去找拆迁办协商吃闭门羹的场面。
在追求“大调解模式”的路上,笔者呼吁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源头、上游,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源头治理。比如,补偿方案民主决策的深入化,听取意见、召开听证会等程序要落到实处,而不是搞形式、走过场。
又比如,提升征收部门一线工作人员、拆迁公司从业人员的调解意识和法治意识,杜绝其“拿着鸡毛当令箭”的骄纵心态,从而在房屋拆迁补偿争议的前调解时代向前一步走。
在明律师最后想提示广大的被征收人,审前和解制度是一项有新意的制度,在实践中,被征收人可以考虑运用此种制度在开庭审理前寻求法院主持下的协商沟通,而不要对此产生抵触情绪。而更为有效、务实的和解、调解,则应当贯穿整个征收拆迁程序的始终。有些时候,解释、说明、沟通多了,决定就会转化为协议,诉讼案件便有望化解于无形。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网络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给与以更改或者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